�k���g(sh��)�W(xu��)У�fǧ���f���@һ��(g��)“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ı����ڠI���IJو�(ch��ng)���g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“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����ɽ��У�Ľ̾��͌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Ǖr(sh��)���ı��(y��n)��Ҫ��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һ��(g��)��(n��i)�̕�(hu��)�W(xu��)��ɢ����ֱȭ������[ȭ�������ȭ��߅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ȵ�һϵ�Є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(n��i)Ҫ�̕�(hu��)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g(sh��)�еĴ̄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(d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섦���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ϵ��Ҫ�I(l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(n��i)Ҫ�̕�(hu��)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g(sh��)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ص����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Ƶ����õ���һϵ�м�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낀(g��)��(n��i)Ҫ�̕�(hu��)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g(sh��)�Д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ѡ��g����һϵ�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낀(g��)��(n��i)Ҫ�̕�(hu��)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軨����Ҫ�c(di��n)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Կ࣬���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�Ҫ��(y��n)�ӹ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Ҫ����ɽ���g(sh��)�W(xu��)У�����g(sh��)Ӗ(x��n)��ץ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(qi��ng)Ӗ(x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У�_ʼ�ˡ�
����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ܸ��ȿڣ����R�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ܶ��^�壬�ܖ|�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……
�W(xu��)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ֵė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|����S�Ĝ؝����}�|�ی��ąǴ����Ϳ�־�ڵȵȶ�ʮ�ֳ�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1995�긣��ʡ�ھŌ��\(y��n)��(d��ng)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У���ɽ��У�״νM�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ӣ���־���ڴ�ِ�Ы@�����g(sh��)ɢ��52���)(j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ɽ�ڴ�ِ�в���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̖(h��o)�������ͻ�������@Ҳ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У�����g(sh��)ِ���еĚvʷ��ӛ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ȫʡِ�º��ı���Ǻ�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ʹ��ɽ��У�����g(sh��)ˮƽ����һ�Әǡ����Ǿ��_չ����ɽ��У“���Ԫ”��(zh��ng)�Zِ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zh��ng)�Zِ����ِ̭���k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(j��)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У���ӣ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ԇ���
��(zh��ng)�Zِ�ĽY(ji��)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ֵė�ȫ���@����“���Ԫ”�Q̖(h��o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У��(ji��ng)�o��ȫ���ɂ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Ī�(ji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i��ng)���üt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ø����ϲ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@��(du��)��(ji��ng)�����ؼ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H�у����@�ɂ�(g��)��(ji��ng)���[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ڵ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“���Ԫ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(ji��ng)���ӌO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ϵė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(hu��)��ο���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⣬���骄(ji��ng)Ʒ�ăɱ��Pӛ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Ҳ����ã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ڸߏ�(qi��ng)Ӗ(x��n)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У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g(sh��)ˮƽ�����w�ϴ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(d��ng)�겿�(du��)���f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g��)���g��ס�M�˽̾�������ώ��͌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gһ��K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x��)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j�(ch��ng)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ǿô��Ř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ƵđҒ����L�L�̶̵�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һУ֮�L�ď��ı��ۿ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g����s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ò���ҕҰͶ�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ε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I������߅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õĿ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߅����Ŀ����ÿ��g�s�Ǻܴ�ġ������ﷴ����(f��)��(f��)�ر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^�Ľ�(j��ng)�M(f��i)�^��ԣ�ˣ���һ��Ҫ����U(ku��)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chu��ng)У֮ʼ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X��ãã�˺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ʮ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ذ��e�X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зų��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Լ���ؔ(c��i)�a(ch��n)����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@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õ��@һȦ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oֵ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ܰ��Լ��ͽ̾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Ѻ�ɡ��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Ԯ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Ǵ�·�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У���ֱ������Լ�һ�˳��Xһ�˳����k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ق�(g��)���О顣���H�e������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y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Լ�Ҳ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У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춼�ڞ���ҡ����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B(y��ng)�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̎����Ӳ�Dz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ط�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k���@�l·�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^�D��(qi��ng)��·�����Լ��V�_(d��)ͨ��֮·��
�o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ı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f��)��(f��)“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߅��ɽ�𡢲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y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Ǿo�o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ҷ���ăɿڏU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˲��ܛ]��һ̎���_(t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_(t��i)�ڠI��?j��)?n��i)�ǽ����˵ģ�ֻ�ܰ��@�ɿڏU�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(t��i)�õ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̾����ώ���ȫ�wͬ�W(xu��)�l(f��)��̖(h��o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п��e�����ȫ�w��ɽ�˶�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ǃɿڏU��?m��ng)~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Ͷ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в��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g(sh��)�W(xu��)У����ɵĴ�������_(t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~����ַ�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ĺ�ȥ̎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_(t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L���ı�ָ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扦���ϕ����ľ��䣬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f��“ӛס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һ��Ҫ��P(y��ng)��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ྚ�书����v����£���(zh��ng)����У……”
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༉(j��)Ҳ���ˣ����L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У��협�(y��ng)�΄�(sh��)׃�������Ҳ협�(y��ng)���L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��ɽ�ČW(xu��)����һ�ČW(xu��)�侚�䡣�ћ]�ܺܺÌW(xu��)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W(xu��)�A�εĺ��ӂ������г�4��(g��)�༉(j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քe�������;b̖(h��o)��“�����R”�Լ�����δ���ގ���̌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4λ�Ļ��n�̎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ؓ(f��)؟(z��)�༉(j��)����Z�ġ���(sh��)�W(xu��)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n�y(t��ng)�y(t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@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W(xu��)У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
�M���_�O(sh��)��4��(g��)�༉(j��)���Ļ�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��g(sh��)”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w��У�L��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У�̾��͌W(xu��)���Џ�(qi��ng)�{(di��o)��“��ɽ���g(sh��)�W(xu��)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W(xu��)�䣬Ҫ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u��ͻ��“���g(sh��)”�@��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���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͛]����ɽ��У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w�̌W(xu��)��(n��i)�ݵ���ɽ���g(sh��)�W(xu��)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¶������g(sh��)�̾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]�����J(r��n)���@��ʲ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Ǖr(sh��)�H�еĎ�λ�Ļ��n�̎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У“ָ�c(di��n)��ɽ”�����ֻϣ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Լ����l(xi��ng)�����Ė|���غ����ꂀ(g��)��ʮ��ʮ�����a(b��)“����֮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ڌW(xu��)У����“�W(xu��)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���“��”��(d��ng)�^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o�P(gu��n)�o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̾������Ҳ�o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f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λ���Ժ����S÷�h��ɽ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Ў����I(y��)�����ڹ����W(xu��)У�ν̵Ď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��˼����ؚ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(j��)��ʮ����ˣ���һ��Ĺ��Y��56Ԫ������ڶ���Ҳ��71Ԫ�����r(n��ng)��ĸ�ĸ���ֵ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ώ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(di��n)��Ϣ�����ׂ�(g��)“�~��”���B(y��ng)�B(y��ng)�ҡ������Ɏ�ʮԪ�Ĺ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(y��ng)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̝�������ю�æ�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ű����x�l(xi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ݚ�D(zhu��n)�ˎׂ�(g��)�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g(sh��)�W(xu��)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Ȏ����N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У���Ӵ����W(xu��)УҪ�o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Ļ�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Ű����@��(g��)��Ҏ(gu��)�Ď������I(y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Z�ĺ͔�(sh��)�W(xu��)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ڽ̌W(xu��)��ɫ���У�L���ı�o���_��ÿ��300Ԫ�Ĺ��Y���ѽ�(j��ng)�Ǽ��l(xi��ng)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У�������屶����ÿ�������@ô��Y�����ڴ�����Xһ���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¶�����һ�B���nƱ�Ļؼ���@��Ҳ�㌦(du��)����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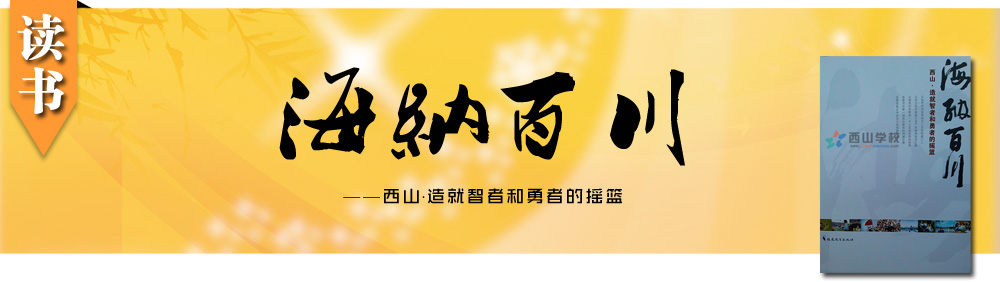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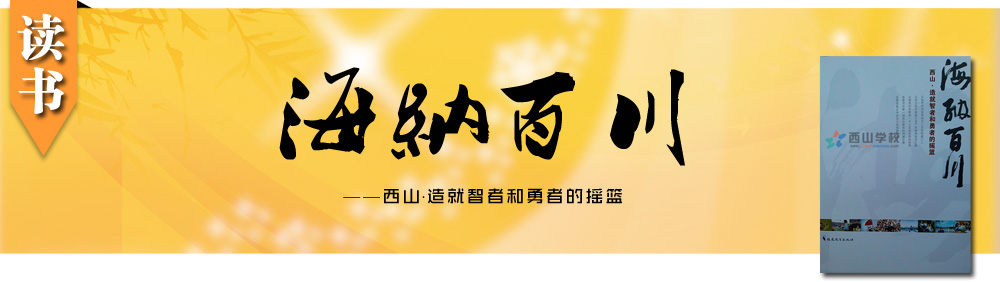

 �}���W(w��ng)���� 35018102000197̖(h��o)
�}���W(w��ng)���� 35018102000197̖(h��o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