��Ŀ�����־���ֵ����_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M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ܳɾ�δ���ČW��……
��ɽ�WУС�W��һ�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,��ô����ô�ÿ������
�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һ�����ĵġ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27�q���겻�����ˈ���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Ҳ�]̫���⣬�s�]�뵽С���ϳ��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ˇ��ص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Ӳ��Ӿ͵�סԺ��ˎ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ֻ݅�ǃ��ֵܣ�С�幫һ�����|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d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ҿ���]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ص��ļ��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f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Ͽ���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Ñõ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Ҳ�]�����ĉ�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Ψһ�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䌚һ����@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XѪ˨�ѽ�(j��ng)�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|(zh��)�֘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ȿ옷�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ȡ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Ȼ�����ҵ��^���˺͂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옷��Ȼ�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njW�I(y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(ji��)����һ��Ҫ�o�����҂��ÌWУ����ƴ��ƴ��Ҳ�ðу������B(y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z���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˴�·�M�����ݚ�D(zhu��n)ǧ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……�쿴�ˎ�ʮ���W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M�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ԏV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֮���l(f��)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Ϸ��Ľ����|(z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ҕ�Ͽ����˸�����ɽ�WУ�ďV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ֱ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ɽ�WУ������ס����ɽ�WУ�д����M�M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@�WУ��һ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@�WУ��Ȼ�Ǻ������n���ϵĽ̎��J��̕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n����Ľ̾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Ѻ��ӂ��̵ö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Ϻ��Ļ��n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Ϻ����g(sh��)�n�w�|(zh��)�ã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�Ը����
�M���ѽ�(j��ng)��Ҋ�錍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z߀�Dz�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Ǿ͵���߅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WУȥ�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WУ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ћ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����{(di��o)���{(di��o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D�z���ڴ��R·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|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Ҋ��·�˾͆��f�@һ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WУ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˹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һ��ʮ��·�˶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Rˢˢ���f��ɽ�WУ�á���D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ɽ��“С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@�Ɇ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Լ�����Ц����·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·�ˁ��Ԗ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ā���“С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
��(j��ng)�^˽�L��“�����{(di��o)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D�z���٪qԥ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־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͵���ɽ�W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䌍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ю״��˵�ϣ���и��o����ɽ�WУ����
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ֹ������Ӹ߷�������ɽꇵ�������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|���\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ɹ�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I�Y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һ�d�ķ������\�ݲ�ֵ�X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ѽ�Nѽ�ȵȎ���Ҿߺ�һ�K�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˂�ʮ�fԪ������@ʮ�fԪһ�֞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Ԫ�مR����ɽ�WУ���郺�ӏ�С�W�����еČW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�һ���µĵ�С�c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͟o̎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ľ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\���_��С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ٍ�cС�X�Թ�ÿ�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όW���½�Q�ˣ������ĸC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D�z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¸�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ڸ�����ɽ�όW�ˣ����Ә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ɳ����˃��ӵ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Ψһ�Č�ؐ�O�ӣ������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Σ�һ�굽�^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˿��^����(ji��)��ǰ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˾͵�Ҋ��Ĩһ�ɴ��ۜI�����ֱĨ���c�O��Ҋ�������Ҋ���˾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Ǵ���ϱ�D�߷��쎧�������ߣ�һ��Ԓ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ӵ�ǰ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
ĸ�H�߷�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ǘӌ���̫�^���M����Ҋ��ɽ�WУС�W��ҪƸ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֕��@�T��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�M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ӵ�ͬ�r߀�зݹ�������ͦ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x���x�أ��xУ�L������@�Ї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߀���@ô����ɽ�WУ�����ȈA�����ҵĉ�����Ҳ�o������?gu��)�݅��һ���貵�ϣ����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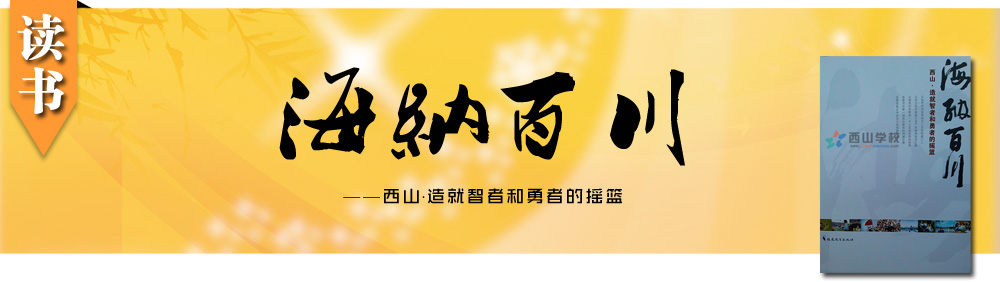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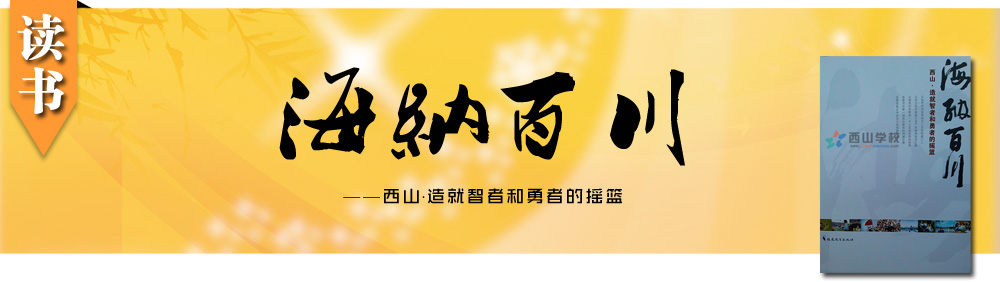

 �}���W(w��ng)���� 35018102000197̖
�}���W(w��ng)���� 35018102000197̖